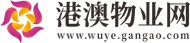天天时讯:与建筑成本相比大多数建筑仍然提供更便宜的刺激
2023-03-20 13:03:52 来源:互联网亚伦·贝茨基(Aaron Betsky) 在“ 意见”专栏中表示,像汤玛斯·希瑟威克(Thomas Heatherwick)通往纽约的互连楼梯这样的巨大公共艺术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纪念碑。臭名昭著的毕尔巴鄂效应可能是伟大的建筑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最后一口气。埃菲尔铁塔和帕台农神庙,华盛顿的购物中心甚至哈利法塔(Burj Khalifa)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昨天那些纪念碑真好。
面对现实吧,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建筑物来刺激和放松我们-或任何其他事情。我们可以在线进行社交,技术可以使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保持舒适和安全,我们可以从周围的模因和图像中获得认同。而且,如果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公共的,统一的东西,或者仅仅是一个宏大而怪异的东西,足以使我们脱身,那么艺术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资料图】
【资料图】
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建筑物来刺激和放松我们
在最近的$ 150万船的公告中,托马斯·赫斯维克楼梯无处定于在曼哈顿的办公室发展,清楚地表明,装置艺术终于迈出了架构,即公民纪念碑的最后堡垒定义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和社会。比大多数城市古迹更大,更昂贵,它在Wow Factor方面也更好。
接管是突然的。尽管您可以将眼镜的建筑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但是直到20世纪初,诸如詹姆斯·特雷尔(James Turrell)这样的艺术家一直在发展效果的阶段和对建筑的沉思分解。达到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以至于在小规模范围内它们都可能真正有效。
现在,Turrell可以将酒店和博物馆变成万花筒,以对抗昼夜节律和明暗变化,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影响我们对空间感知方式的色调。
尽管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是2014年Turrell最为精巧的装置的所在地,但正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Turbine Hall成为了真正的引擎,通过它,奇观艺术不断在公众意识中发动,并渗入他们的心中。
从2000年奥卢法尔·埃里亚森(Olufar Eliasson)的黄色太阳开始,这个广阔的空间-至少建筑师可能会想到-应该足以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已经成为了巨大的抽象和幻灯片的场所,这些抽象和幻灯片将我们所有人变成了孩子。与Eliasson和艺术家Carsten Holler的复杂性相反,蛇形画廊的年度实验已变得微不足道,这些实验已成为建筑反对这些装置的对立面。
反对Olufar Eliasson和Carsten Holler的复杂性,蛇形画廊的年度实验似乎微不足道
真正在人们的意识上刻画了这种新艺术的一件作品是“豆子”-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的抛光镜面圆环,叫做云门,他于2006年在芝加哥千禧公园安装了它。最终的自拍磁铁。
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作用确实是对芝加哥进行了总结:弯曲的表面上映照着的著名摩天大楼,成为每个在那拍照的人的光环,使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美国大都市中的一员。
在过去的15年中,这种安装工作变得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当Turrell开始使用频谱变化的电灯时,在艺术世界中,鲍勃·迪伦(Bob Dylan)相当于在纽波特爵士音乐节上演奏电吉他。
同样,埃里亚森也用水,简单的棱镜,有时甚至是用阴影的墙壁来交易精致的作品,以换取复杂的建筑,这些建筑来自柏林的工厂式车间,雇用的人员比该城市大多数优秀建筑师都要多。
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在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设计安赛乐米塔尔轨道时,达到了人们认为可能或好的极限。塔特林(Tatlin)的《第三国际纪念碑》(Peruage to Third International)毫无意义地存在于人们的眼中,但它既作为眼镜又是美学对象而失败。它太大了,太糟糕了。
现在,像希瑟威克(Heatherwick)这样的艺术家正在将媒体提升到新的高度和比例。他似乎能够吸引大量资源,用于水上公园,花园桥和剪楼梯。
与建筑成本相比,大多数建筑仍然提供更便宜的刺激
很难想象,这一切始于(至少在公共领域)是12年前在伦敦海港拐角处展开的小人行天桥。到现在为止,这些眼镜的总价是巨大的,至少与我们过去用来购买公共艺术品的价格相比是如此。
与建筑物的成本相比,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仍然提供更便宜的刺激,正是因为他们可以专注于提供这种体验。
做得好吗 那要看。在我看来,艺术家控制尺寸和复杂性的难度与建筑师一样困难。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可能甚至是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形式,材料,功能元素以及细节的实践,无法像训练有素的建筑师那样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大部分都植根于沉思中,它变得越活跃-与船只相比,就越没有那么活跃-它从最大的力量中发现自己越远。
曾经让我们实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的原因–既是因为我们在集体集会或足球比赛中一起体验某些东西,又是因为我们正在感知到无限和令人惊奇的东西–现在涉及到许多小发明和如此多的活动使这些作品很多都像是成年人的游乐场,而不是我认为这种艺术会提供的替代宗教经验的场所。
这种玩味也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力量。船只改造了通常隐藏在建筑物内胆中的设备,该设备可以使我们起身或下楼,或帮助我们逃生作为消防梯的灾难,然后将其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体玩具。
它还采用了楼梯作为完美的舞台布景的方式,在舞台上可以观看和观看,进入和观看正在进入的入口,这些空间不仅保留给歌剧赞助者,新娘或政客,还包括办公室工作人员午休时间。它美化了乐趣和无用的魅力。
我最喜欢的作品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会涉及到更多方面。它使我们成为对作品成功至关重要的演员。
这些作品很多都像成年人的游乐场
走进蒂诺·塞加尔(Tino Sehgal)的《变奏曲》(我在2013年的卡塞尔文献展(Kassell Documenta)展览上看到了该变奏曲),发现自己与一个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跳舞,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振奋的,亲密的和社交的经历之一很长时间。
进入Elmgreen&Dragset的舞台布景就意味着要成为一些反常戏剧中的演员,就像他们最近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的《明日世界》中一位死去的建筑师一样。
当这些眼镜发挥作用时,它们可以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体验作为社区的某些事物。我们不再是孤立艺术品的观察者,也不是沉闷的建筑的盲目用户。
艺术使我们脱颖而出,将我们凝聚在一起,重塑和振兴我们的公共生活,而且,不重要的是,让我们一起玩乐。在老大哥一直在观看的城市剧院中,我们彼此敬畏,正如我希望船只能够做到的,任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艺术都值得每一分钱。
它表明,即使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艺术家以找到社会建筑的精髓,建筑中仍然存在着生命。
标签:
相关阅读
- 天天时讯:与建筑成本相比大多数建筑仍然提供更便宜的刺激
- 楼市重回复苏通道 更需重视需求“断层” 今日聚焦
- 私募新品发行“冷热不均” 量化指增类备受青睐
- 楞迦 速递
- 当前时讯:50万失业人口,将近1%的经济收缩,英国将会是下一个日本吗?
- 西媒文章:非洲已厌倦欧洲家长式作风
- “吹哨报到”为基层治理解难题
- 嘉峪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3月19日嘉峪关疫情最新消息今天数据统计情况通报-全球快看点
- 报春“消息树”开花,北京赏樱攻略来了!|天天热门
- 脊柱包虫病 (vertebral hydatidosis)-今头条
- 镜鲤的习性_镜鲤的习性和经济价值|今日热闻
-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是_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当前简讯
- 世界观点:社区搬运合同范本(必备34篇)
- 环球热消息:我被pua了是什么意思(被pua什么意思)
- 守望先锋steam下载_守望先锋steam叫什么
- 新动态:259luxu - 1355_259luxu系列十大极品
- 海豚救人_海豚为什么会救人
- 凯迪拉克xt6怎么样汽车之家论坛(凯迪拉克xt6怎么样)
- 当前观点:海西塑胶地板多少钱_海西塑胶网
- 清晨运动的好处
- 极乐寺直播_极乐寺_焦点关注
- 淡水河谷:首批签署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25x25宣言”
- 世界今日讯!新能源燃油配方(新能源燃油)
- A00级小车市场之争,熊猫mini迅速上位,QQ冰淇淋处境不妙-世界实时
- 天天滚动:花粉症与感冒有区别!提前应对有妙招
- 邓伦资料个人资料_说一说邓伦资料个人资料的简介
- 费迪南德:贝林厄姆可能会更倾向于加盟皇马
- 自制芝麻花生糖的做法_花生糖的做法
- 福耀玻璃2022年度核销的坏账准备金额为4500元
- 提振信心共促公平 开封示范区举办2023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
Copyright © 2015-2023 港澳物业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京ICP备2023022245号-31 联系邮箱:435 226 40 @qq.com